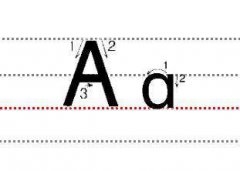1930年秋,徐志摩辞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职务。 应胡适之邀,任北京大学教授,兼任女子师范大学教授。 他住在胡适家里,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照顾。 不过,他对上海的陆小曼还是很在意的,让她来北京的时候,她也拒绝了,徐志摩只好频繁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。 1931年上半年,他来回走了八趟。 这不仅增加了他的思想压力,也增加了经济压力。
这段时间徐志摩和她的书信往来主要有两个内容:一是劝陆小曼北上与他重逢; 另一个是谈钱的问题,希望她能减少开支,稍微减轻他的压力。
首先是钱的问题。 起初,徐志摩觉得来京后,努力赚钱,收入并不多,足以养活他和陆小曼。 他跟陆小曼算了一笔账:“北大的教授(300元)早点订了,没什么问题,就是我的课比中大的多,不是很开心。”再说了,还是个问题,他们本来是聘我做大学女教授的,那是两百八十,北大也就六百不远了,可惜教育部最近严禁兼职教授了。其实挺难的,但是不能兼职,如果只读兼职的话,工资很少,六点半一个月才一百五十,最好是兼职也能当教授的女大,那我不管别的了,有两百八三百,只要不拖欠工资,我们两个人永远都能过得去。”
算盘打得不错,陆小曼却没有按照他的算计,在上海花钱毫无顾忌。 徐志摩只好求她尽量省钱。 1931年6月14日,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说:“其次是钱的问题,我急得睡不着觉。现在,我首先希望的是薪水早点发放假了,不过节前寄到上海,节后。而且260元一眨眼就到。家里开张支票,两个月的房租300多块。。过节不算。不知道怎么凑一百块。我真的很犹豫。我想有外快的钱帮忙(徐志摩为了赚更多的钱,竟然帮人家卖房拿佣金——小太记),可惜暂时没有成功,和一切都浮在云端,怎么办?金钱太可恶,来之不易,去之也太容易。
接下来,依旧是算账的事情,但就连劝说和哀求,也已经是声势浩大,感慨万千,令人动容:
“从公历三月份开始,我不算自己的使用费,路费等等,但是我已经给银行和你家付了钱,我已经有两千五十块钱了,如果我再寄四百和过节五十元,就是二千五百元。而且到六月底只有四个月。如果公债能顶400元,那就有3000元。按照一个月500元,你应该是小康了,可惜还有欠债,上个节你拿了300块钱,我这个节拿了260块钱,就去560块钱儿童学习网,结果落得水深火热,后来,我和老家分手了,没啥可做的,你就迁就吧。我想想,我们夫妻真是觉醒了!你再按规矩办事,实在是不可理喻。再说了,我当初答应过你的一个月五百块钱给你家用,专供,我只打算教书,还有别的事翻译的话,两百可以靠,两者加起来,平均接近六百,而且仍然易于维护。 我不想看到过去六个月的一切都颠倒了。 妈妈去世了,我来回奔波,像缠着帆的风。 Bi(雅)是怎么翻译的? 原来学校给的只有500多块钱,第一个月就扣了一半。”
”亲爱的姐姐:你觉得我这样的处境很难吗?同时,你好像连五百都不够,那怎么办?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并考虑一下。” 长久之计,以免浪费脚和脚,总是洗不干净。 在家庭使用方面,第一是“房子”,第二是“车”,第三是“厨房”。 这三样东西是可以省的。 在我看来,所有家庭的经济水平都很难达到每月400。 姐姐,如果你真的能帮到我,你就替我想想办法吧。 反正我有多余的钱,我是绝对不会自己存起来的。 我靠工资过活,当然不能梦想存钱,唯一的希望就是减少债务。 欠债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,你知道的,有时候连最好的朋友都会因此受到伤害,我非常害怕。”

徐志摩与前妻所生的儿子阿欢,与前妻生活在一起,并不在他眼前。 他真的很希望再要一个孩子。 不过,嫁给陆小曼之后,她一直没有生育过孩子。 一是陆小曼贪图享乐,心思根本不在这里; 二是她也是个酒鬼和吸鸦片的人,根本不适合生孩子。 于是,他只能低声哀求陆小曼:“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那种福气,为人父母,带孩子的福气。放不下是行不通的,我们都得想一想。” ,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,我想如果你愿意,我愿意为我的孩子牺牲一些,努力戒酒,我省的是鸦片,即使孩子长大到一定程度,如果你再吃饭,你以为我们有,还真是时候。”
其实此时的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关系,绝对不仅仅是陆小曼贪图奢侈的问题,而是他们关系的问题。
徐志摩对陆小曼的感情是毋庸置疑的,即使在陆小曼对他毫无同情的时候,他的痴情也从未改变。 不过,至于陆小曼对徐志摩的感情,就不好说了。 当然,陆小曼一开始肯定是喜欢徐志摩的; 然而婚后,两人的感情鸿沟却因生活习惯、审美情趣、处理人际关系方式的差异而逐渐拉大。 尤其是翁瑞武的出现,更是让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 在这件事情上,陆小曼几乎没有顾及过徐志摩的感受。
徐志摩北上的时候,一直希望陆小曼跟他一起去。 陆小曼一身体不好,他就很担心。 他们两个在一起,可以给她更好的照顾; 其次,让陆小曼离开上海,可以缓解经济压力,同时也可以趁机除掉翁瑞武。 第三,徐志摩也需要陪伴和关怀。 为了达到让陆小曼北上的目的,徐志摩美言劝说、严厉训斥、利诱、求饶……想尽办法,可惜陆小曼还是不为所动.
其实,徐志摩心里也清楚秋 徐志摩,陆小曼离自己越来越远了,但他也无能为力。 虽然我还没有放弃努力,但是希望越来越渺茫了。 他的内心也充满了怨恨和怨恨,逐渐表现在他的书信中。
夫妻感情好,片刻不愿分开,天涯海角相随; 更何况,陆小曼没有工作,也没有事业上的联系; 起初,徐志摩以母亲无人照顾为由,立即指出,这根本不是问题:
“我觉得只要你愿意来,就不会是在你长辈那边,而是完全在(你的)旧习惯上。回到过去确实很难,也确实是你会在爱中感动... 只要这次你能相信你的爱 即使是你的牺牲 也为我牺牲 即使你离一个地方很近 我觉得也不好一天都离不开它,再说北京真是个好地方,你太固执了,就算你这样迁就一次,到北方来一会,一言不合,你可以回去了,你不丢脸吗?”
徐志摩越说越难过,甚至想起了过去种种不堪的事情:“我们这对夫妻真的很特别:一方面,你我为彼此所受的苦难和牺牲,不能说是微不足道。年轻的情侣有我们的脚跟;但另一方面,既然如此相爱,为什么又舍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分开?你大度当然大方,但总有一个常识事情。几年前,想想都觉得可笑。我是个白痴,你总是知道的,你真的不知道我有多渴望和你一起散步,或者出去吃顿饭,或者一起看场电影,羡慕别人。可奇怪的是,我守了好几年,却一个机会也留不住。你每天都没有空,我们只是没有单独过。直到最近,我已经部分麻木了,我不要那种世俗的快乐。甚至在我离开之前,今天是我的生日,而你不知道。 我想和你一起吃顿饭,玩得开心。 临走前我说了好几次我想至少(至少)有一次约会,但最后我还是走开了,单次约会是不允许的。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?”

在另一封信中,徐志摩写道:“老婆,我不在的时候你一点都不想我吗?现在能把我陪在你身边真是个例外。你整天都在吃饭,从起床到睡觉,到闭上眼睛,吃吧。也许你想芒果或洋白果比想师父(徐志摩指自己)更深情更迫切。师父是头牛,他唯一的用处就是工作赚钱——而且有点可怜:奶牛不仅要上两周课,还要补课,晚上还睡不着觉!心里不踏实。 “天气不好,我会满身是灰!夫人,一个字都不忍传吗?”
在另一封信中,徐志摩抱怨说因为陆小曼的不留神,自己差点没衣服穿:“我家真是糊涂了,我一共能有多少衣服?现在那两个单兵哔叽都不在箱子里了!真是热,我只有一件白大衣,没钱在这里做。还有那件羽纱,你说你染了然后做的,你做了吗?……你自己主人的衣服,求你保重其中一时,我也没有人商量,做好了就立刻送去,等着戴上。”
至此,其实爱情和婚姻都走到了死胡同。
也算是命中注定,两人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和计划以后的路怎么走,路一下子就断了。 1931年11月19日早上8点,徐志摩乘坐中华航空“济南”号邮政飞机从南京北上。 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地区时,顿时大雾弥漫,航向难辨。 为了找到准确的航线,飞行员不得不降低飞行高度。 不料,飞机撞上了现在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古云湖街道的开山,随即坠入山谷。
如果徐志摩没有坐飞机,他也不会死于空难。 那么,他为什么不坐火车,而坐飞机呢? 道理也很简单,坐火车要花钱,坐飞机免费。 徐志摩在写给陆小曼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:“老实说,往返机票我已经卖了,我现在正在借钱生活。我在拓新海帮我飞回来了。这不是说我愿意冒险,真的是为了省钱。” 而且上次坐飞机也是免费坐中华航空邮政济南飞回北京的。
回京前,徐志摩和陆小曼大吵了一架。 最终,徐志摩实在忍无可忍,只好扬长而去。 11月18日,徐志摩抵达南京,入住张新海家中。 晚上和张新海的妻子韩香梅等人聊天。 徐志摩穿着一条腰间破洞的小短裤,到处找丢失的腰带,引得众人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他还自嘲说自己抓起来匆匆穿上就走。
说笑间,韩香梅忽然似有预感:“芷墨,明天要是有事怎么办?”
徐志摩回以一笑,问道:“你不怕我死吗?”
“志摩,说真的,小心点,司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?”
“不知道,没关系,我一直想飞,我还以为天气好,适合飞呢。”
“小曼这次有没有说你的航班?”
“小曼说,如果我死在飞机上,她就是风流寡妇。”
旁边的杨杏佛道:“个个寡妇风流!”
一切都是命运。
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婚姻以失败告终。 关于这一点,徐志摩自己也承认。 正如胡适所言,徐志摩冒着巨大的风险秋 徐志摩,历尽千辛万苦,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、亲情和名誉,去追寻和考验梦想的神圣境界,而最终,一场残酷的失败在所难免。 他的失败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。
1931年徐志摩去世后,陆小曼年仅28岁。 徐志摩的死对陆小曼打击很大,她认为徐志摩的死是她的原因。 从此,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很少外出活动,大部分时间都在整理徐志摩的遗作。 她和翁瑞武开始同居,但她还是拒绝正式嫁给他,大概是对徐志摩的愧疚吧。 陆小曼的晚年很凄惨。 昔日的才女,因吸食鸦片,牙齿掉尽。 翁瑞武破产后,连日常生活都出现了问题。 1965年,他在贫困中去世。 生命的尽头只有一个请求,希望与徐志摩合葬,被徐家人拒绝。 火化后,陆小曼的骨灰无人认领,被遗弃。 直到20年后,她的侄女才帮她建了一个衣冢。
2023年4月1日,北京。